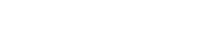西藏文物在北京举行的特展中,展出了一方象牙质地的印章。
在众多璀璨的展品中,这方小小的印章显得颇不起眼。但它的背后,却凝结着一段结构宏大的历史画卷。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方印章,以及它背后的三世达赖喇嘛!
.png)
这枚象牙质地的印章体量很小,兽钮右边镌刻着大明万历戊子年制的年款。万历戊子年对应的是公元1588年(万历十六年),记住这个年款,我们后面要说一个与此相关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左侧镌刻钦赐朵尔只唱图记,“朵尔只唱”为藏语“持金刚”之意。
很有意思的是,印纽左侧镌刻为“尕尔只唱”是个明显的笔误,“持金刚”在藏语中读作“多杰羌”,而蒙古人在读藏语音时,经常有点大舌头。
于是便出现了,从“多杰羌”到“朵尔只唱”的读音,等从蒙古读音到汉字,又不知经过了怎样的转折,从“朵”变成了长得很像的“尕”。
但在之后的相关记载和论述中,都无一例外的记做“朵尔只唱”,可见“持金刚”的藏语,发“ga”的音是不靠谱的。
.jpg)
一、“达赖”尊号的由来
作为这枚印章的主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历代达赖世系中并不十分显眼。
他既没有五世达赖的艳阳之盛,也不像六世达赖那么幻化多情,但他却是西藏历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
他以自己的抉择,给整个格鲁派指明了方向,是个不折不扣的,灯塔级的人物。
谈及索南嘉措的影响,我们还得从当时格鲁派面对的政治局势说起。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西藏弘传教义时,获得了当时西藏地区统治者帕木竹巴政权的青睐。
格鲁派早期创建的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都是在帕竹政权首领和家臣的资助而成。
但花无百日好,天无百日晴,十六世纪初期帕竹政权逐步衰落,自己的一亩三地都快混不明白了,哪还有闲工夫继续支持格鲁派?
而敢于和帕竹政权叫板的仁蚌巴、辛厦巴(藏巴汗),所信奉的都是噶玛噶举,对于打击格鲁派一直都是不遗余力。
在这种风雨飘摇的背景下,格鲁派被迫采用了活佛转世体系,来稳定自己的教派传承。(格鲁派接受活佛转世制度,在各教派中相当晚。)
正当格鲁派承受重压之时,1578年(明万历六年)索南嘉措收到了,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领俺达汗的邀请。
在接到邀请的一瞬间,他是不是想到了萨迦班智达和阔端的凉州会盟,以及之后萨迦派的巅峰胜境,我们不太清楚。
但作为一个坐困愁城的宗教领袖,索南嘉措决心牢牢抓住这次机会。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高瞻远瞩看到格鲁派的危机,当索南嘉措宣布即将远赴青海,教派内部出现了大量反对的声音。
五世达赖便在自传中写道:“当时发生了争执,索南嘉措对一些侍从很不满意,有意再不返回拉萨。”[1]
.jpg)
忽必烈与八思巴
蒙藏两位领袖在青海湖边一见如故,决定互赠尊号增进友谊,俺达汗赠与索南嘉措的尊号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好长的一个尊号!
这个尊号由五个部分组成:
“圣”,是超凡入圣,即超出尘世间之意;
“识一切”,是对藏传佛教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僧人的尊称;
“瓦齐尔达喇”,是梵文“执金刚”之意,是对藏传佛教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僧人的尊称。
“识一切”和“瓦齐尔达喇”结合起来,是说索南嘉措在显宗、密宗都取得了最高成就。
“达赖”,蒙古语是大海之意;
“喇嘛”,藏语是上师之意。[2]
这是“达赖”一词第一次被用于修饰某个人,而索南嘉措尊享了首发的荣耀!
“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对西藏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
但如果问这个词,是怎么蹦到俺达汗脑子里的,估计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首先得说“大海”这个蒙古词,肯定不是因为两位在青海湖畔,面对浩浩汤汤、连接天地的湖景,触发灵感而成。
这两位心思缜密的领袖,不会干这么无聊的事儿,所谓互赠尊号早就是事先想好的。
这就像二人闲聊时,俺达汗“不经意”的谈及——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友谊,索南嘉措何等心神,闻得蒙古弦歌,焉能不知雅意?
他微微一笑,说道:“我等非只今日,曾世世相会。汝为成吉思汗孙胡必赉彻辰汗(忽必烈)时,我为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3]
俺达汗听得心花怒放,二人间的关系瞬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段对话,如果被锦衣卫的卧底听到,估计万历皇帝要睡不着觉了。
身为蒙古王族没事跟人聊忽必烈,你想干啥?!
尤其是你脑袋上,还顶着明朝顺义王的帽子!
跟明朝有关的事情,我们放在后面说,还来说“达赖”这个尊号。
这个尊号,很有可能是由索南嘉措的名字而来。
在藏语中,“嘉”可以理解为广阔、广大,“措”则泛指水体、湖泊。
“嘉措”就是大水面的意思,在古代藏族的认知中,对海洋是没有多少概念的,毕竟青藏高原离海洋太远了。
索南嘉措四个字合在一起,是“福德如海”之意,俺达汗估计早就心里有数,才会赠了达赖这个尊号。[4]
.jpg)
内蒙的五当召
二、重塑藏传佛教的地位
达赖世系因此有了名号,这件事虽然很重要,但也就不过如此。
毕竟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办成了什么事情。
这两位首领的青海之晤,不但接续了由萨班、阔端开创的蒙藏关系,还再次奠定了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心中的崇高地位。
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位超然,但自从朱棣将元朝皇帝撵到漠北牧马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日渐式微,萨满重新成为蒙古信仰的主体。
要知道,成熟的宗教是种高等级的信仰体系,需要有相应的物资基础匹配。
而蒙古人在重回草原游牧后,失去了支撑国家经济的来源。
国家的政治系统,从元朝的封建+奴隶的混合体,跌落为更原始的部落联盟状态。
因此,发生经济基础不能支撑上层建筑的状况,也属正常。
在蒙藏领袖青海之晤后,索南嘉措在俺达汗的配合下,重塑了藏传佛教的地位,这才是他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而这实际上是,蒙藏两族精神上的第二次合流。
正是因为,藏传佛教重新成了,蒙古全族的主流信仰。清朝入关后,才会形成了满蒙藏三族互相牵制、互有需求的政治三角型关系。
否则,即便是藏传教派有心投附,说不定清朝皇帝,还得掂量掂量您的斤两,值不值的下此重注!
.jpg)
三、明朝与青海之唔的关系
蒙藏两族领袖聊天聊的愉快,明朝跑过来给了索南嘉措一枚印章,这是几个意思?
这事儿和大明朝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
蒙藏两族领袖在青海湖边会晤,大明朝廷早就得到了密报,俺达汗对藏传佛教的种种尊崇之举,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了然于心。
他忽然发现,明朝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说不定有了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这个明朝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俺达汗本人。
.jpg)
说起来,明朝真没有明粉口中那么强大,蒙古军队打到北京城下除了大家熟知的“土木堡之变”外,还有一次“庚戍之变”。
庚戍之变的主角便是俺达汗,为了平复俺达汗的进攻,明朝被迫“通贡互市”与蒙古人贸易,并册封俺达汗为顺义王。
开通互市后,俺达汗确实不在明朝北部折腾了,他带着军队向西拓展,打跑了青海的蒙古瓦剌部,这才有了他和索南嘉措的青海之晤。
俺达汗经略青海的举动,明朝不愿意了,本来只有北部边防承压,这下西部边境也得加小心了。可让他回自己老巢丰州滩(呼和浩特附近),又迟迟不见动静。
.jpg)
张居正得知索南嘉措在蒙古这么有面子,感觉俺答汗的问题,可能有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索南嘉措得知张居正的意图后,拍着胸脯保证,“妥妥的,包在我身上!”
(“有阁下吩咐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
还别说,索南嘉措确实有能力,次年俺达汗便离开青海,回了蒙古属地。
事情办成后,索南嘉措曾亲笔致书张居正,“合掌顶礼朝廷,钦封于大国事阁下张(张居正):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体甚好。我保佑皇上,昼夜念经。……压书礼物:……”。[5]
令张居正有很挠头的事情,索南嘉措抬抬手就给办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俺达汗的影响力。
正因为索南嘉措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诸番莫不从其教”),再加上确实曾为明朝办过事儿。
俺达汗去世后,继任顺义王扯力克(俺达汗长孙)上书明廷,请求册封索南嘉措为“朵尔只唱”,明朝非常爽快得便答应了下来。
这便是此方印章上,藏文“持金刚”(朵尔只唱)的由来。
.jpg)
四、跟印章有关的其他内容
这方印章的背后,除了上述几点外,还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值得说上一说。
有藏文史料里记载,“明朝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遣使臣在内蒙,敕封索南嘉措为‘朵尔只唱’,并邀请他入京面圣。”
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这方印章右侧明明白白的刻着“万历戊子年制”(万历十六年)的年款,考虑到索南嘉措万历十六年三月,便在进京路上圆寂,明使只可能是万历十六年初见到的他。
你很难想象,明使在万历十五年带着敕书来到内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一顿念,念完了跟索南嘉措说:“不好意思,章还没刻好,等你到了北京,我再给你啊!”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使臣混成这样,离死也就不远了。
.jpg)
俺答汗
藏史记载索南嘉措受封为“大觉禅师”或“灌顶国师”,也是不准确的。
参考《明实录》的记载,获封“大觉禅师”的另有其人,而“灌顶国师”的说法,则全无踪影。
考较诸多史料,五世达赖喇嘛修订的《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较为详实和可信:“明朝中央政府在索南嘉措,1579年(万历七年)前往甘州会晤甘肃巡抚侯东莱后,曾授予他“护国弘教禅师”名号,并颁赐封诰和印信。”
可见,明朝在封授索南嘉措“朵儿只唱”名号和印信之前,确曾另行封授过名号并赐予印信,只不过并非所谓“大觉禅师”、“灌顶国师”,而是封授的“护国弘教禅师”。
这是为明朝对达赖喇嘛世系最早的封授,也是达赖喇嘛系统与明中央政府正式建立关系之始。[6]
需要注意一点,明朝曾有硬性规定“未获封‘国师’及以上封号的藏教领袖,无权入京觐见”。
而作为只拥有“护国弘教禅师”和“朵儿只唱”封号的索南嘉措,被使臣邀请进京,意味着明朝已经认可他“国师”的地位和重要程度。
如果他在万历十六年,成功入京面圣,以他在蒙古的影响力,获封一个“国师”称号,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惜,索南嘉措在入京途中圆寂,无缘获此尊号。
.jpg)
最后,索南嘉措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
如果不是他亲身入蒙弘传佛教,估计就不会有个蒙族孩子名叫云丹嘉措(四世达赖喇嘛),而格鲁派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还真不太好说。
世事云波诡谲,领袖殚精竭虑,在后辈看来,不过是层云归鸟、入目繁花。
但历史碾过的沟壑尚在,一枚小小印章的背后,便有这么多艰辛和求索。
现在它静静的躺在展柜之中,雷霆乍惊的过往,您听到了吗?
参考书目:
[1]、《五世达赖自传》__陈庆英、马连龙、马林;
[2]、《安多政教史》__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
[3]、《蒙古源流》__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
[4]、《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生平事迹新探》__陈庆英;
[5]、《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八、《达赖喇嘛传》__牙含章;
[6]、《历代中央政府封授达赖喇嘛印信考述》__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