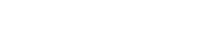.jpg)
第1编
从远古到唐宋:西藏历史起源与中华文明一体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的,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西藏地方自古是中国一部分,藏族与世居青藏高原的古今许多民族为开发、建设和守卫祖国的西南边地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灿烂文化的发展谱写了不朽的华章。西藏地方的藏族和祖国内地的汉族及各兄弟民族,也在共创中华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紧密关系。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历史,走进那让人心潮起伏的遥远过往。
第1讲 汉藏同源的历史脉络
关于西藏地区人类的来源,藏文史书中有许多神话传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卵生说。该传说称:“在太极之初,有一个由五种宝贝形成的卵。后来卵破了,从中产生出一个英雄,这位英雄长有狮子的头,象的鼻子,老虎的爪子。他的脚象刀一样锋利,毛发象剑一样坚硬。头上长着两只犄角,犄角中间栖息着鸟王大鹏。”由此传出了人类。
另一则更有影响的传说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传人的神话。该传说称,在远古时期,有一只猕猴生活在西藏山南泽当一带的山林中。后来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到贡布日山洞中修行。有一天一个女魔前来引诱,并对猕猴说:“我俩结合吧!让你我享受人间快乐!”猕猴一口拒绝。罗刹女威胁道:“你若不与我结合,日后我会成为妖魔的伴侣,到那时,一天将伤害上万个生灵,一夜将吃掉成千的众生,再生下无数的魔子妖孙,雪域之境将成为魔怪的世界。所以,恳求你发善心,答应我做你的妻子。”猕猴于是产生矛盾心理:我若与她结亲,就得破戒;若不与她结亲,将引发祸害人类的后果。该如何处置呢?据说,犯难的猕猴来到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前,请予引导。结果,菩萨让他与罗刹女成婚。于是他们成为夫妇,不久生下六只小猴。父猴带他们到果林中以野果为生。三年后,当父猴再去探望时,小猴已繁衍为五百只了。林中的果实已被吃尽,众猕猴啼饥号寒,模样十分悲惨。
老猕猴又来到观世音菩萨面前求助。菩萨道:“你的后代由我抚育。”说罢,便从须弥山缝隙中取出青稞、小麦、豌豆、荞麦、大麦种子播撒在大地上。大地长满不种自生之谷物。众猴得到了充足的食物,吃了谷物之后体毛也逐渐变短,尾巴也逐渐消失,并能够直立行走,相互交流出现了语言,逐渐变成了人类,他们就是青藏高原地区的先民。
传说毕竟是传说,何况是被佛教史家修改得面目全非的传说故事。但是,古代西藏地区先民对人类来源的解读,并且与自身生存的环境结合起来的叙述,对于后人认识西藏早期历史还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群众喜闻乐见并口耳相传赋予其无穷的魅力。
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结束了认识史上的神话传说时代,为人们科学认识西藏地区早期历史提供了扎实的依据。特别是对认识西藏地区和祖国内地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支持,以便让人们看清楚西藏早期历史的发展线索,以及源和流的关系。
一、卡若遗址中的历史线索
对于青藏高原地区的早期历史,学术界有很多的研究,而考古成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历史研究中,更为古代西藏地区的历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为廓清迷雾、还原真相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西藏地区科学的考古研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7年,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卡若村有一个巨大的考古发现,该古代遗址被定名为卡若遗址。卡若遗址的发现整体上推进了青藏高原早期历史研究,学术界更清晰地认识了西藏地区早期历史研究的部分面貌。有考古学者指出,“昌都卡若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是西藏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从此奠定了西藏原始社会研究新的起点,揭开了以真实可信的实物资料来重新‘书写’西藏远古历史的新的篇章。”这些成果同样也为我们展现了青藏高原地区和内地密切交流的过往。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遗址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4000—5000年,分别经过1978年、1979年、2002年三次发掘,是考古界公认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被命名为卡若文化。1985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昌都卡若》一书,作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九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卡若遗址发现有房址、道路、石墙、石台、石围圈、灰坑等遗迹。出土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装饰物等,还发现有炭化的粟米和动物骨骼等。通过考古学者的研究,逐渐揭开了西藏早期历史的面纱,大大丰富和更新了人们对青藏高原早期历史的认识,这些内容比文献记载要丰富得多,也灿烂夺目得多。卡若发现的双体陶罐,器物造型饱满优美,构思巧妙,工艺娴熟,代表了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被誉为西藏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代表作。
.jpg)
图为卡若双体陶罐
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卡若遗址半地穴式的房屋,实际上它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仰韶文化向西向南延伸的产物。卡若出土的石器之器形、纹饰以及陶器,特别是彩陶,又和仰韶文化中的马家窑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在卡若遗址还发现了只有中原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才独有的一种古代的植物——粟。包括家畜、猪的饲养也反映了仰韶文化西进、南进青藏高原的线索。在卡若遗址还发现了贝壳类的东西,学者们猜测它很可能扮演着那个时代货币的功能。仰韶文化的年代,学术界目前确定为距今有4000—5000年的历史。通过梳理,能清晰地看到: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距今有8000年,随着逐渐地往西推进,7000年、6000年、5000年,这个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如果把这些资料跟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中原文化的西传南传还有一条脉络,就是大家熟悉的丝绸之路在中国国内西南段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它同时还是丝绸之路与横断山区民族走廊互相交织的产物。中原文明在西进的过程中,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也就是黄河上游一带,有一条路线转向南下,沿着横断山区的民族走廊,到了今天的西藏昌都市。卡若遗址的发现反映出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承载着古代一段历史和文明,以及相互持续交流的过往,根据这些资料和其他的证据,学术界有专家得出一个结论: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从空间距离来看,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相距遥远,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可以说困难重重,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止内地与西藏地区人民之间交往的步伐,从出土考古实物来看,双方的文化联系依然源远流长、文明互动根深叶茂。事实上,对这一史实不仅古代汉文资料有记载,藏文资料有记载,考古资料有反映,而且民间传说也有体现,可以相互印证。汉文史书记载,先秦时期,西羌有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闲。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闲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新唐书》即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
即使在考古资料方面,不仅是卡若遗址的考古发现,而且西藏高原地区其他重要考古发现也有反映,比如拉萨地区的曲贡遗址、西藏山南的昌果沟遗址、昌都的小恩达遗址、藏北草原细石器游牧文化遗址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藏高原地区的早期历史特征,以及它和中原地区的相互联系。
二、汉藏语同源的史实依据
中原地区和西藏高原的联系还远不止于此。实际上还可以从语言学者的研究,特别是原始汉藏语同源研究的成果中获得支持,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关于汉语和藏语同属于一个语系即汉藏语系,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共识,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原始汉语藏语和人是同源的。关于这个论题,国内学术界、国际学术界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美国学者包拟古的《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一书,讨论了“原始汉语与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罗列了485个相互关联的藏汉语字,指出在周朝时期已经存在的汉藏同源词。中国学者俞敏教授的《俞敏语言学论文集》一书,制作了一个“汉藏同源字谱稿”,共收录约600个同源字,发现藏语(吐蕃语)和春秋战国齐人(姜姓,神农氏后裔)语极像,而且不只限于词汇。俞敏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后来学术界不断有人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语言研究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很重要的支持,人们还发现,语言的相同事实上反映的是汉藏两族都与古羌人存在密切的关系,中原文化,特别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明,即所谓华夏族的祖先,实际上和古羌人有着传承关系,大夏的建立者叫大禹,司马迁《史记》记载“禹兴于西羌”。后来周朝的建立者同样跟古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称为姜,学者们都认为姜和羌实际上是古代同一个民族,或者同一个渊源。
史书里关于藏族的祖先吐蕃人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是“吐蕃本西羌属”,即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是西羌的后裔,是古代西羌人的后代。汉代学者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羌,西戎牧羊人也”。古羌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羌族一个民族,而是古代很多民族共用的一个称呼,或者从事游牧业生产、有着诸多共性特征的一群人,后来被中国多个民族所吸收,成为他们的族源之一。这其中就包括今天中国的汉族和藏族,这些就是从语言上进行同源分析的最为扎实的基础。
因此,文献资料、考古发掘也包括相关的语言学研究都证明,汉族和藏族在血缘上、语言上,包括文化上,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有着深厚的基础。
三、密切交流的文献追述
关于汉藏之间的密切联系,汉文史料还有一些记载,当然这些记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前面引证的“无弋爰剑”,也就是羌人的领袖,受秦人扩张的推力,逐渐越过析支河到了今天的西藏腹心地区,最后形成了吐蕃人。这也是史料的一种说法,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说法,比如说鲜卑部拓跋人进入青藏高原,形成了吐蕃,“拓跋”和“吐蕃”读音相同,所以史书中称其部落为“吐蕃”,是古代的一种说法。尽管还有商榷的空间,但是反映了古代先民或者史学家对两个民族之间血缘方面的联系是有考虑的。文献资料记载和考古资料显示,古羌人和藏族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的分布范围也高度重合。古羌人不仅活动在青藏高原,而且还活动在新疆南部地区,包括许多民族和部落。吐蕃崛起后在吸纳古羌人的同时,也吸纳了青藏高原及周边很多民族和部落,同样是多源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在此得到很好的体现,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民族学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诸多启发,比如古羌人的猕猴崇拜风俗,包括他们对游牧文化、农业文化的贡献在史料中也是有迹可循的。他们活动范围广阔,迁徙频繁,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给予了推动作用,古羌人和今天中国的很多民族都有血缘联系,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从后代的汉文史料记载,也包括藏文史料记载对这段早期历史的追溯中也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藏文文献对汉族、藏族包括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均有相应的记载,在一些藏语词汇中也留下了两个民族或者多民族在这块土地上互相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痕迹。
四、基因研究的科学佐证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人类早期历史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试图推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寻找历史的痕迹。这些痕迹可以从多个学科去分析,比如历史学、历史语言学、考古学甚至古生物学,还有人类学、气象学、进化遗传学等等。但是这些学科所告诉我们的时间纵深度是不一样的。比如,历史学可以使我们上溯到4000年前,这四千年已经上溯推衍得很远了,像甲骨文就是上溯推衍到3000年之前。历史语言学则通过语言的比较,去发现语言是如何进化、怎样分化的,最多的年限可上推到6000年前,如果要推到10000年前,则要借助一些猜测了。考古学因为有实物保存,从现在的学科发展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250万年之前。而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进化遗传学可以推得很远,因为人类和黑猩猩作为两个物种在进化上分开是在距今500万年到700万年之间。历史可以通过史籍研究去推测、了解,但史前史一直是遗传学和考古学的强项,尤其是遗传学,因为它基本上在推测史籍上没有的东西。”这些研究是值得关注和期许的。目前,中国科学家和美国以及西方一些科学家组成团队,对人类的古代谱系做了一些分析研究,即通过DNA来辨识古代人种和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些成果也为我们认识藏族的起源,藏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藏族、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条途径。
基因学的分析发现,汉族跟藏族在基 因学M122、M134这两个因素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两个民族分开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具体的数字有的学者认为可能距今有5000年,也有的说法是4000年,但是不管哪种说法,其共同的一个观点是:在基因谱系中这两个民族分开的时间是比较近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血缘联系是比较密切的。
基因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东非,目前发现进入中国的南亚语先民分化路线有三条,共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在云南,一个是珠江流域。其中一支沿着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他们最终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时候到达河套地区、黄河中上游盆地。这批汉藏语系的祖先也被后人称之为先羌,他们也就是汉族与藏族的共同祖先。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扩增新的居住地。汉藏语系的两个语族开始分野。其中一个亚群在M134的基础上又发生了M117的突变。他们带着这个突变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华人,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汉人。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他们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羌、彝、景颇、土家。
这种联系虽然只是科学领域提供的一个侧面印证,但是它与前面提到的考古学上的资料、文献中的记载、传说中的一些故事,以及语言学上相互关联的事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吻合或者互补之处。
这种文化联系给内地与西藏高原地区的民族及文化间的交往交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后来人们看到的汉藏文化圈、西部文化圈就包括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诸多联系的遗痕。
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也影响到西藏文明发展的趋势,这就是所谓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问题。青藏高原的南边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它的主峰是海拔8844.86米的珠穆朗玛峰。它是一个年轻的高原,但是翻越它即使对今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古代文明交往的趋势与规模。它的西部同样是一个高大的山系即喀喇昆仑山脉,北边则是昆仑山脉。有一个地方相对开阔,并成为联系外界的重要通道,这就是它的东边或者东北边,这个通道可以说俯身向内,我们前面提到的民族文化交流,不论是丝绸之路的东西方连接还是民族走廊的南北沟通,实际上它的交汇点或它的主要活动地段都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地区,这一自然环境也为青藏高原地区藏族的先民以及青藏高原地区各个民族的先民与内地的联系提供了广阔的通道,在自然环境上就有一个天然的、良好的基础。
有的学者认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实际上与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从西藏古代文明来讲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它的东北地区,东北方是敞开的,我们看到青藏高原地区的文化后来也相应地向内地不断延伸。
中原文化进入青藏高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良好地理条件而得以增强的,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有时还十分曲折。自然科学界、考古学界也包括历史学界从不同的角度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包括来自内地华北地区的人怎样进入青藏高原,怎么越过唐古拉山这样高大的山系,突破高原缺氧的条件,进入西藏腹心地区,甚至适应高原,产生基因方面的某些细微变化,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不同成果却可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为我们认识古代的文化交流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
五、宗教文化的内在联系
古代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还可以从宗教文化联系的角度来审视,也就是说古代时期的原始宗教在青藏高原地区或者周边地区存在的状况,以及它们与内地的联系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青藏高原地区的苯教,大家知道苯教是青藏高原地区土生土长的宗教,尽管对其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对它发展阶段的划分也不尽相同,但是青藏高原地区原始苯教的一些基本内容、崇拜方式以及一些神灵系统,大家还是有一定共识的,比如说崇拜日月、崇拜自然、崇拜动物,也包括崇拜祖先,等等。
关于猕猴祖先崇拜,汉文史料里提到过古羌人奉猕猴,以及羱羝为大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猕猴作为祖先崇拜的一部分,是动物崇拜的内容,同时又把它作为祖先崇拜。还有一个就是羱羝,就是公羊,是对公羊的崇拜,这也是古羌人精神信仰的一部分。
这些崇拜的内容跟中原地区古代对自然、对动物,也包括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存在很多内在的联系。这和前面提到的文化交流、人员迁徙有关,也与考古发现、基因证据所呈现的方方面面相互联系有关。
18世纪,藏族著名学者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在他的《土观宗派源流》一书中,就把古代青藏高原地区的苯教与中原地区的道教密切地联系起来。他认为苯教的创始人敦巴辛饶,或者辛饶米沃,其实就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君,认为两者是合二为一的,道教的“仙”正是苯教“辛”(gshin)的来源,苯教和道教只是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反映而已。他的这个观点并非突发奇想,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事实基础。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道教的发源地或者早期的核心地区是在四川西部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是与西藏、涉藏工作重点省及内地十分密切关联的地区。
汉代的文献对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包括宗教方面的联系已有所反映,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大力宣传汉朝政策,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影响很大。当时,“白狼王、唐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即《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歌颂汉朝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这首诗由一个叫田恭的官员译其词语,并由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到都城洛阳。反映了古代川西、藏东地区与内地的密切联系。
一些印度学者发现,《度母秘义经》《风神咒坦多罗》《摩诃支那道修法》《弥曼山坦多罗》《梵天坦多罗》等几部婆罗门教梵文文献,都提到印度密教中与救度母崇拜或独结母崇拜有关的“女人道”(Vamacara)来自中国,印度密教中奉行的“五真性”供养也与中国有关。《度母经》和《风神咒坦多罗》还提到在公元4世纪时,伐湿斯塔(殊胜,Vesistha)曾亲赴中国向道教徒学习“摩诃支那功”。印度泰米尔文文献记载,南印度密教的18位“成就者”中有两位是中国人,泰米尔名字叫博迦尔(Bogar)和普里巴尼(Pulipani),他们于公元3世纪时去印度传播道教符咒、医术和炼丹术等,博迦尔曾带弟子回中国学习,学成后又回到印度。
学者们注意到老子的《道德经》等经典从中国唐朝传入印度东北地区和佛教密宗在这个地区此阶段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也就是说佛教在印度东北地区发展时期大量地吸收了道教的一些仪轨和内涵,所以它在尚未传入西藏地方之前,已经具备了道教的元素。进入西藏地方以后,佛教进一步与苯教发生联系,互相吸收、互相结合,使西藏佛教具有了更多的区域化特征,区域化特征中也就包括了中原道教文化的元素。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指出:“乍视之下,密宗似乎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汉文史书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义表乃告以中国未有佛法以前已有圣人(指老子)说道。童子王请译为梵言。太宗乃命玄奘法师与道士蔡晃、成英等共三十余人集于五通观翻译《老子》五千言为梵文。奘与晃、英等颇多争论。’这里清楚记载了唐太宗命玄奘翻译老子《道德经》并赠送给东印度童子王的史事。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其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西藏地区和道教的发源和繁荣之地四川邻近,也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开展频繁和深入的交流互动。
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地区存在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沿长城一线西抵河湟,然后向西南弯折,沿青藏高原东侧南下,直至云南西北部。在这条路线的途经范围内,生态环境有诸多相似之处。从考古发现上来看,其考古遗存表现在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随葬器物、出土动物骨骼以及其蕴含的古代人群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相似之处颇多。这就是介于农牧文化之间的一个传播带,从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到青藏高原北部地区,通过人员交流、经济交往、贸易联系始终保持着一种畅通的状态。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纽带。
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远隔高山大川,复杂的气候和恶劣的条件并没有阻隔内地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也包括西藏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边疆地区,乃至东北边疆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