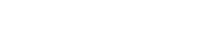作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近年来青藏高原不断考古出土新的吐蕃时期墓葬,它们等级不同、形制各异,但却体现出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章主要对青藏高原新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墓葬,以及墓葬制度、习俗等加以分析。从中可以窥见青藏高原本土的文化因素和来自中原、河西地区的文化因素相互交织融合,体现出7—9世纪生活在这里的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若干历史片断,为认识吐蕃时代的墓葬制度与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青藏高原;考古;吐蕃墓葬;交往交流交融;高原丝绸之路
中国考古学从近代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总书记用最精准的语言,总结了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回顾百年历史,中国考古学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是边疆考古的兴起和发展。作为祖国西部边疆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的青藏高原,虽然现代考古学进入这一区域的时代相对较晚,但却在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近年来,青藏高原的重要考古收获层出不穷,时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各个历史时期,均有重大的考古新发现问世。本文拟就青藏高原新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7—9世纪)墓葬加以分析和评述,从中提出对其墓葬制度、丧葬习俗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等若干问题的新认识,进而探讨青藏高原各族群与周边地区在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线索和相关证据。
一、高等级吐蕃墓葬的新发现及其主要特征
7世纪,兴起于雅隆河谷的吐蕃悉补野部族通过不断的兼并、征服,逐渐统一了高原各部,建立起强大的唐代地方政权吐蕃王朝。吐蕃王朝从其建立之初,便向中原唐王朝学习,创立文字,输入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制度文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加强。吐蕃墓葬制度也开始成形。笔者曾经总结归纳从史前时代(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到吐蕃王朝时代青藏高原考古出土的各类型墓葬,认为其发展到吐蕃王朝时期,以吐蕃王陵(今西藏山南琼结县境内,俗称“藏王墓”)为代表,效仿唐代帝陵制度,已经形成了“主流型”的高等级墓葬,从地表封土、墓室结构、随葬器物、杀牲祭祀、殉葬陪葬等一系列丧葬程序上开始具有制度化的特征,并影响到青藏高原各地。
但是,由于过去在青藏高原各地,尤其是在今西藏自治区经科学考古发掘的吐蕃时期高等级墓葬极为罕见,笔者的许多推测都还建立在汉藏文献提供的线索上,未经考古实物相对应证实。近年来,先后在青海都兰、乌兰和西藏当雄等地出土了一批等级较高的吐蕃时期墓葬,对于我们深化对吐蕃墓葬制度的理解提供了帮助。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青海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先后被评为2020、2021两个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发表有考古发掘简报,西藏当雄墓地资料尚未正式公布,但已有部分资料披露。基于这批新出土的重要考古材料,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特征。
1.地面墓园与祭祀建筑 位于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拉萨当雄墓地,有迄今为止在吐蕃王朝中心区域内首次发掘出土的高等级墓葬,意义十分重大。据现有资料披露,此次发掘共清理出6座大型封土墓和33座小型封土墓,大墓分布在南区、小墓分布在北区,对墓园应该是有一定布局和规划的。从现已公布的M3号墓航拍照片上观察,在墓葬封土的外围有两重近方形的茔墙相围绕,应是墓园内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一)。由于地表破坏严重,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已无法观察到原来是否有墓园建筑的遗迹。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地表墓园遗存为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墓园平面近方形,由东西长33米、南北宽31米的茔墙围合,茔墙均为平地起建,下部用青石块砌筑,上部以土坯垒砌,茔墙上开设有门道和排水口,门道内还残存有木质的门构件,包括木门砧和门槛。
.jpg)
图一 当雄吐蕃墓M3
墓园内有的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建筑遗址。如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的祭祀遗址位于墓园的东北隅,包括两个房间(分别编号为F1、F2),F1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由石墙围合,北墙上开设有门道,门道内残存有木质门砧和门槛,地面经过人工处理,残存有小石块和红烧土的遗迹。F2平面呈方形,也是由石墙围合,东墙上开设有门道,门道内铺设有大石板。发掘者根据在房间内发现成堆的羊肩胛骨、墙体上有的插有羊肩胛骨的现象推测,“可能是与祭祀有关的痕迹”,应当可信。在墓葬封土和茔墙之间形成的廊道,可供后世祭拜者在举行祭祀、参拜活动时绕墓而行,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的茔墙与F1、F2可以相通,或许暗示着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上人们可以在绕墓祭拜之后,再在特定的场所进行祭祀活动。过去笔者曾在西藏地区考古调查发现的墓葬地表上发现有石砌的墓垣、茔墙等遗迹现象,在墓葬封土丘的一隅也发现过房屋建筑的痕迹,推测其当为墓园与祭祀建筑的遗迹,但终因缺乏直接经过考古发掘获得的证据而无法确认,新的考古资料证实了这一推测。
2.封土建筑形制 高等级的吐蕃时期墓葬往往都在地表留下了封土的遗迹(所以这也成为后世盗墓者的显著标识,导致“十墓九空”的被盗现象发生)。拉萨当雄墓地大型封土墓的封土立面均呈覆斗形,封土平面基本呈圆形或圆角梯形。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因已多次被盗和回填破坏,墓室已经向下塌陷呈锅底状,所以无法认定原来封土的情况。但是,此墓为热水墓群的大型墓葬之一,与过去考古发现的另一座“热水一号大墓”(当地俗称“九层妖楼”)紧相毗邻,两者相距不远,均在同一墓区内。这座“热水一号大墓”是典型的依山建墓,封土呈覆斗形。由于这两座墓葬在墓主身份等级、族群关系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由此推测,2018血渭一号墓原在墓室顶部也应修筑有覆斗形的封土,因后期严重盗扰破坏才没有留下痕迹。乌兰泉沟一号墓的情况和2018血渭一号墓相似,据发掘者观察“墓葬可能原有地表封堆,但遭盗掘和回填的破坏,遗迹已无法辨别”。结合西藏各地发现的吐蕃时期墓葬情况来看,在墓室之上营建平面呈方形、梯形、立面呈覆斗形的封土坟丘,已经成为墓主身份等级、社会地位的体现,与吐蕃之前的石板墓、石丘墓、石棺葬等墓葬在形制上区别明显,是这个阶段“主流型”墓葬的重要特点之一。
3.墓室结构与布局 与既往主要基于地表调查勘测的墓葬考古工作情况相比较,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新收获是由于上述这批墓葬均经过全面的考古发掘清理,从而可以了解到地下墓室的结构与布局等情况。其中,拉萨当雄墓地的几座大型墓葬的墓室结构颇具代表性,其中有的为竖穴土坑石室墓,有的为穹隆顶式样的洞室墓,两者均为多室墓,由墓道、前室、后室、侧室等组成,如上文中提到的M3,即平面布局呈“十”字形。类似这样的两种墓葬形制,竖穴土坑石室墓起源甚早,西藏史前时期的墓葬多见此种类型;而穹隆顶式的洞室墓应是高原人们模仿居室毡帐式样发展起来的新的墓室形制。进入吐蕃时期之后,两者分别成为这一时期西藏高原最主要的墓室结构。2018血渭一号墓是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室结构规模最大、形制复杂、装饰风格独特的一座高规格墓葬,它既有吐蕃腹心地带高等级墓葬墓室呈格状的多室墓结构,但又在主墓室内四壁皆设斗拱类木结构、绘制彩色壁画、砖砌棺床。这些作法,则为西藏地区吐蕃墓葬所不见,究其源头恐不一定来自西藏本土,笔者将在后文详论。拉萨当雄墓葬中也发现有用木料覆盖墓室顶部的作法,这和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常见的做法相似,表明两者之间在营建工艺和用材上似有一定联系(图二)。
.jpg)
图二 2018血渭一号墓内部结构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的墓葬形制明显不同于上述两地,此墓墓室前室用青砖砌筑,后室和两侧室分别用方形柏木垒砌,形成一座砖木混建的多室墓葬。最为奇特的是,在此墓后室西壁外侧墓坑壁上,用木石结构还建了一处近方形的“暗格”,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其中出土有一件方形龙凤狮纹鎏金银冠饰和一件金质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杯,应是墓主特殊的营葬方式。乌兰泉沟一号墓在墓内四壁的砖木结构上均绘制壁画,使用彩绘棺椁作为葬具的做法,也和拉萨当雄墓地的基本风格不同,某些方面和2018血渭一号墓相对较为接近,反映出更多青海本土的文化色彩(图三)。
.jpg)
图三 泉沟一号墓平剖面图
总之,这批较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掘,从地面到地下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体现出7—9世纪之间唐代吐蕃墓葬的主要考古学特征,并且首次在西藏与青海两地的吐蕃墓葬之间建立起可以参互比较的标尺,改变了既往研究主要依靠传统汉藏文献对吐蕃高等级墓葬内部状况进行推测的局面。同时也证明,过去文献记载称吐蕃赞普陵墓外形“墓形堆四方形”“宛如牛毛帐篷”等描述大致可信。文献对其墓室内部情况的描写虽然多带有夸张、神秘的色彩,但墓室“宛如九宫格”般的多室结构,在不同的室内随葬以不同的随葬器物,将王者生前的服装、王冠随葬入墓等说法,也具有一定真实性。
此次在拉萨当雄首次发掘的大型吐蕃墓葬虽然与山南琼结藏王墓在规模、等级和格局上还有较大差别,尤其是地表是否存在石碑、石象生之类的设施还不见披露,无法确认死者的身份、地位,但总体上仍然体现了吐蕃时期各地王公贵族以藏王墓为模仿对象,墓上建有墓园,封土呈覆斗型,墓室内部具有竖穴多室、仿生人居室的穹隆顶式结构等重要特征,这为认识吐蕃王朝时期最高统治者赞普陵墓为代表形成的、具有等级区别和一定规制可循的墓葬制度文化,也提供了难得的参照物。
青海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的身份,由于棺床内出土了一枚由双峰骆驼图像和古藏文组成的印章,经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CT扫描后,得以清晰地识读其古藏文内容为“外甥阿柴王之印”,所以可以基本比定墓主是吐蕃占领下吐谷浑邦国之王、吐蕃墀邦公主之子莫贺吐浑可汗,这也为进一步认识青海吐谷浑故地与吐蕃王朝关系密切的高等级墓葬的丧葬礼俗和墓葬制度,提供了首例科学证据,其意义同样十分重大。正因为这座大墓虽然属于吐蕃统属之下的吐谷浑邦国的王陵,所以一方面具有诸多和西藏本土吐蕃王陵相似的文化现象,但另一方面也具有浓厚的青海本土文化色彩,可以初步认定为吐蕃文化和吐谷浑文化相互融合而成的墓葬规制。虽然墓葬盗扰严重,但由于“318大案”的破获以及随后考古工作者及时的抢救性清理,留下大量遗迹、遗物和丧葬文化现象,从中可以观察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存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的墓葬形制明显不同于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因在此墓的“暗格”中发现鎏金银王冠,由此可以初步断定其同样属于吐蕃王朝时期吐谷浑故地的高等级墓葬。发掘者推测,此墓的选址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之上,俯瞰开阔的河流谷地,与西藏和青海地区其他吐蕃时期墓地选址理念是基本一致的,地表很可能也存在一定规模的封土墓丘,“而从所遗留的扰土堆积来看,应该不存在典型的吐蕃墓葬所流行的梯形石围结构……很可能体现了一种源自本土的丧葬传统”,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对于死者的身份,发掘者推测其“可能是一位对唐朝文化高度认同的吐蕃贵族”,对此尚有可商之处。但总体而言,此墓和这一地区其他多座曾经出土过所谓“吐蕃棺板画”的墓葬一样,可能代表了吐谷浑故地在吐蕃占领之下,既保留了深厚的唐朝文化影响、同时也深受吐蕃文化影响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丧葬习俗。
二、社会普通阶层墓葬的多元特点
这里所说的“社会普通阶层”墓葬,是相对上文所述的高等级墓葬而言。在青海都兰热水墓地内,除了前述的“都兰一号大墓”和新发现的“2018血渭一号墓”这样的高等级墓葬之外,还分布着一批墓葬等级相对较低、可能代表着当时社会中下层人士的墓葬,其中以2014年发掘的都兰哇沿水库古代墓葬群为典型代表。
哇沿水库坝体位于都兰县热水乡扎麻日村东南约2公里处的察汗乌苏河两岸山前台地上,2014年为配合水坝修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墓葬25座、殉马坑5座。目前已有考古简报发表,发掘报告也将不日问世。发掘过程中,笔者曾亲赴考古现场考察,留下的一个最为深刻的印象,是这25座墓葬规格不高,除其中一座M17可列入中型墓葬(与本文所论的大墓相比较)之外,其余均为小型墓葬,但是墓葬形制却十分复杂,所反映出的个性化,或可称之为多元化的特点明显,并无较为统一的墓葬规制可寻。
首先,从墓葬类型与结构上看,这批墓葬中以带有浓厚吐蕃墓葬文化特点的石室墓居多,占据主流地位。这类墓葬往往地表上有石砌边框的封土坟丘,平面多呈梯形,墓室结构多由石砌墙体的墓圹和墓室构成,有的在墓室顶部残存有压顶的柏木,这些做法与在西藏本土和青海热水墓地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墓葬的基本风格一致,反映出在吐蕃王朝统属之下地域文化的共性。但同时墓地中也发现有一座砖室墓(M19),此墓由墓道、墓圹、封门、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道为斜坡式,以石块封门,墓室采用方砖错缝平砌而成,很显然与吐蕃墓葬文化有别,具有河西地区唐墓的特点。此外,墓地中还发现3座木椁墓,整体由圆形石圈、墓圹、夯土台、椁室等部分组成,此类墓葬最大的特点是由石块砌成石圈和墓圹,再用大量预制的木板或方木砌建椁室四壁,最后用柏木方封顶。在建墓的许多细节上,显示出多元的文化因素:如编号为M16的这座木椁墓椁室四壁在用木板砌建时,部分木板的中部及一端书写有古藏文,用以表示木板层的序号,显然是为了施工时不致出错,表明藏文在当时的流行。此墓的底部,又采用了方砖错缝平铺,这又是河西地区唐墓中常见的做法。至于使用大量柏木方封顶的做法,也和这一时期具有吐蕃文化特点的墓葬营建方式相似。
其次,从这个墓地所反映出的丧葬习俗上观察,也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在较高规格的石室墓附近,发现5座殉马坑,不少墓内也有杀牲祭祀的遗迹,这是吐蕃时期动物杀殉习俗的反映。在M16中还出土书写有古藏文的木简,其内容有“(有)头巾等若干”“(有)衣服一件”等字句,其性质可能为记录随死者入葬的“衣物疏”一类的木简。在墓葬中随葬记录死者殡葬过程中的“衣物疏”这一习俗,很早开始便流行于汉地,汉唐时期在河西地区也十分盛行。吐蕃墓葬中出现“衣物疏”之类的文字材料,可能受到中原汉唐文化的影响。在葬俗上,不少石室墓中有火烧人骨的堆积和屈肢葬式,这种古代的习俗在青海地区史前古代羌人的墓葬中便已经出现,很可能延续影响到后世。M25中出现了“锯头葬”的现象,过去在西藏昂仁布马古墓葬中也曾发现“环锯头骨”的现象,笔者据《文献通考》卷334·四裔十一“吐蕃”条下:“人死,杀牛马以殉……其臣与君自为友,号曰共命人……又有亲信人,用刀当脑缝锯,亦有将四尺木大如指者刺两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的相关记载,认为其当与吐蕃时期的殉葬习俗有关。如果这一推测无误,青海哇沿水库墓地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应当具有与之相同的文化背景。在编号为M23的石室墓中,还出土了16件用动物肩胛骨制成的卜骨,表面均有烧灼迹象,上面遗留有5—9个不等的灼痕,并书写有古藏文。其中标本M23:12正面的古藏文文字可以辨识,初步释读为一件关于马匹买卖的卜骨,当中有关于马的毛色、价格、交易双方及证人等内容,其书写格式曾见于敦煌西域一带出土的古藏文文献。用古藏文书写在卜骨表面并随葬入墓,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吐蕃占卜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和当时河西走廊、敦煌吐鲁番一带各民族之间贩卖马匹等交易活动的繁盛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与死者生前的经济活动有关值得考虑。
总之,这处墓地死者的身份等级不高,主要为社会中下层阶级;在墓葬的营建方式上集石室墓、砖室墓、木椁墓等多民族特点于一地,并无一定之规制可寻。在丧葬风俗和随葬器物上既反映出浓厚的吐蕃文化特点,同时又具有唐代中原地区和河西地区的诸多因素。因而可以初步判断,葬于此处墓地的死者绝非某个单一民族,或者换言之,这一墓地绝非是基于某个单一民族文化因素而形成。极大的可能性则是在同一墓地中葬入了不同民族,或者不同文化背景的死者,通过各自的丧葬习俗,曲折地反映出青海都兰热水察汗乌苏河两岸不同族群之间彼此混同、相互融合的文化现象。
三、从墓葬装饰看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如上所述,西藏本土和青海都兰新出土的这批吐蕃时期墓葬,提供给我们观察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若干横截面。由于这批新出土的考古实物材料涉及从高等级王公贵族到一般社会成员的不同层面,所以有助于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范围内来分析这些通过墓葬考古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及其背景。
7—9世纪的青藏高原,由于吐蕃王朝统一高原各部并不断向外扩张兼并,尤其是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重点拓展,敦煌、西域以及青海吐谷浑诸部均一度被吐蕃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所以在这个时期来自西藏本土吐蕃文化的影响在所难免。拉萨当雄墓地的墓葬形制从总体上看,也被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中的上中层人士所采纳;当雄墓地大型墓葬中残存的部分金银器和青海都兰吐蕃墓地出土金银器具有相似的艺术造型特点,尤其是以前仅见于青海都兰热水墓地的镶有绿松石的组合式死者“金覆面”五官构件,此次也在当雄墓地中出土,从而为这类高等级墓葬死者的丧葬习俗和墓葬规制找到了源头,打上了吐蕃文化的烙印。但是,以新发现的都兰热水2018一号墓、乌兰泉沟一号墓为例,从墓葬的营建、装饰来看,一方面以吐蕃文化为主流,但另一方面仍然可以从中发现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痕迹。
热水2018一号墓在墓道和墓圹之间设有照墙,主墓室内设有斗拱类木结构,主室四壁绘制壁画,这些做法均不见于西藏本土吐蕃墓葬。发掘者认为“壁画的施工技法与中原地区唐墓壁画相似”,这是完全正确的。笔者认为此墓主室内的斗拱之上为照墙,形成墓内和墓外连成一体的象征性建筑体,意在模仿生人宅院,与之类似的做法曾多见于河西地区五凉时期墓葬。如敦煌佛爷庙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中,也是在墓门之上设砖砌照墙,照墙基本与墓门垂直,自下而上镶嵌各种仿木构造型砖和雕刻花砖。两者尽管在装饰材料和结构布置上各有不同,但在设计意境上具有共同之处。此外,热水2018一号墓在主墓室内设置祭台、用砖砌建棺床等做法,也均见于河西走廊和青海湖地区魏晋十六国至唐代墓葬,故其渊源很有可能是受到这一区域内汉文化的影响。热水一号墓的墓主人采用彩绘漆棺,这和乌兰泉沟一号墓的情况相同。这类彩绘漆棺一方面与北魏时期鲜卑贵族的丧葬习俗有关,另一方面与敦煌吐鲁番一带汉晋至唐代墓葬中的彩绘木棺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也有类同,所以也应是在吐谷浑传统的鲜卑文化旧俗的基础上,受到了来自河西、西域汉唐文化影响的产物。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乌兰泉沟一号墓。这座墓葬首先在墓葬形制上,采用的是墓道之后接续前、后、侧室的布局,主次分明,这和拉萨当雄大型吐蕃墓、热水2018一号墓等墓室多为并列多室墓的形制都不相同,而体现出较多河西、敦煌地区唐墓的特点,所以可以基本肯定墓主人并非“吐蕃贵族”。但是,死者同时又深受吐蕃文化的影响,体现出不同文化之间混同、交融的现象。首先,从墓葬的营建方式上看,虽然多受唐墓分前、后、侧室等布局结构的影响,但却在构建方式上采用前室为砖木混合,后室和侧室采用柏木砌建,墓顶采用棚木封盖的做法,这些特点和这一区域吐蕃系统墓葬又有相似之处。其次,在丧葬习俗上,墓道填土中发现动物骨骼、鹿角等,还有火烧祭祀的遗迹,墓圹口部填土内发现人殉一具,死者头骨左侧有焚烧痕迹,殉者下方填土中有炭化的烧骨,发掘者推测可能也为一处祭祀遗迹。这些因素都体现出吐蕃墓葬文化当中苯教杀牲、人殉等祭祀习俗的影响。
再从此墓的壁画内容分析,多元文化的特征更为明显。从总体上看,此墓前室残存的壁画全部绘制在白色底面的砖壁上,主要反映仪仗、伎乐之类的仪卫场面,这都是唐墓壁画常见的布局。但具体的画面,却又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例如,前室东壁墓门南侧绘制的是仪仗队列,由于残破过甚,可辨识的人物只有5人,最前方1人手执旌旗,其衣饰特点是头戴圆形盔形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佩戴弯月形刀鞘,袍下出露黑色长靴。其后4人分为两纵列,下方前列第一人保存最为完整,其衣饰特点为头戴幞头,身着交领窄袖长袍,双手合拱于胸前,腰束带,足穿黑色长靴,身后牵有一匹红色的带鞍之马,马上无人骑乘,当为控马。下方第二人大部已残,但可观察到此人也是身着交领长袍,腰束黑带,足穿黑色长靴,身后牵一匹白色骏马,马鞍上铺放有红底黑点的毡毯。上方前列第一人只残存下半身,也是身着红色长袍,袍下出露黑色长靴,手中执有旌旗,仅存旗杆。第二人身着白色长袍,身后牵一匹红色骏马,马上有鞍,铺放有带团花图案的小毯。这几个人物形象均面部丰腴,身材壮硕,无论是服饰特点还是人物、马匹的画法均是一派唐风,人物的身份也并非吐蕃人。但是,这几个人物的面部,都有“赭面”痕迹,即在眼部、额部、两颊等部位涂有朱红色颜料,这是典型的吐蕃文化的因素。在吐蕃占领吐谷浑、敦煌和河西四郡之后,无论何种民族在衣饰和装饰上都要以“吐蕃装”为其模仿对象,这即为其中一例(图四)。
.jpg)
图四 泉沟一号墓前室东壁仪卫壁画残存画面
前室南壁壁画因被盗破损已大部不存。根据留下来的照片资料,可以大体知晓原来绘制的可能是一幅伎乐图,正中一长方形地毯上有3人席地而坐,衣饰特点各有不同:最上方一人身着小翻领长袍,演奏拍板;中间一人头戴圆形盔帽,身穿交领长袍,足穿黑色长靴,弹奏琵琶;最下方一人头缠巾,吹奏筚篥,三人面部也都有“赭面”。乐队的前面还有一人似正在随着音乐起舞。在其周围分别站立数人,衣饰特点均身穿不同花色的长袍,有的在袖口饰有团花,腰间束带、足下穿靴,应是正在观赏乐舞的王公贵族。这支小乐队的成员从服饰特点上看可能既有汉人、也有胡人,也是由不同民族组成(图五)。
.jpg)
图五 泉沟一号墓前室南壁伎乐壁画残存画面
此墓的考古发掘者仝涛先生已经十分敏锐地观察到,此墓在前室墓门口所绘制的仪卫图,“其中牵马侍卫的带旒旌旗、‘虎豹韬’形制、圆领长袍服饰和一手屈臂握拳执于胸前的仪态,都与神龙二年(706)唐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壁画所绘仪卫图一致,只是数量规模不同。在青海地区习见的吐蕃时期棺板画上,尚未出现过类似仪卫图像,因此可以推测该壁画反映的是唐朝高级贵族所匹配的仪卫礼制,在吐蕃贵族阶层内似未广泛流行”。笔者认为这个观察是准确的,从乌兰泉沟一号墓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看,似更有可能系深受唐朝制度文化染化影响的吐谷浑上层贵族所为。
后室壁画与前室壁画最大的不同点,是全部绘制在木头垒砌的壁面上。内容保存相对较为完好的有北壁的“放牧图”和西壁的“帐居图”。北壁的“放牧图”画面的右侧中心为一座带有红色装饰条带的圆形帐篷,其式样与过去在青海都兰海西州发现的多处棺板画上所绘的帐篷式样相同。帐篷的前后各站有一人,虽残损严重,但仍可观察到这两人均头戴盔帽,皆有“赭面”,牲畜群正朝着他们行走而来。画面上牲畜的品种有骆驼、马、羊、牛等,在其最后为一站立者,衣饰特点与帐篷前后的两人相同,也是头戴盔帽,饰以“赭面”,应为同一族属。从这几个人的服装特点来看,和这一地区出土的其他棺板画上大量出现的缠头巾的吐蕃人形象略有区别,笔者颇疑是否为当地“吐蕃化”的吐谷浑人形象的写照(图六)。
.jpg)
图六 泉沟一号墓后室北壁放牧图壁画残存画面
后室西壁的“帐居图”所反映出的多元文化交融色彩尤其浓厚。画面的中央为并列的两处居所,一为带有喇叭形通气孔的圆形帐篷,白色的帐篷上装饰有红色的条带,在帐篷的门口左右各立一人,均“赭面”,拱手于胸前,右侧一人头戴圆盔帽,身穿长袍;左侧一人头上所戴帽子的式样为典型的“鸡冠形帽”,身着交领长袍。这种“鸡冠形帽”也称为“山字形帽”,状若三座起伏的山峦,笔者曾经在讨论青海地区吐蕃墓葬中出土棺板画上人物服饰时指出,它曾是北魏鲜卑族的服饰特点之一,过去在宁夏固原雷祖庙北魏墓彩绘漆棺、山西大同市智家堡北魏墓彩绘木棺上出现过,考古发掘者均指认其为鲜卑族的“鸡冠形帽”,和另一类“垂裙皂帽”同为鲜卑服饰的特点之一,所以孙机先生直接称其为“鲜卑帽”。笔者由此比定,这个人物的族属应为继承了鲜卑传统的吐谷浑人。
在这顶帐篷的左上方和右下方还各站一人,两人的服饰特点也很具特色,左上方人物头缠红色高头巾,身穿红色翻领长袍,腰束带,足穿黑色靴子,双手拱于胸前,是较为典型的吐蕃装束;而右下方的人物却是头上缠巾、身着红色半袖交领衣,下着短裙、内穿长裤,形象与其他民族服饰有别,笔者初步判定其应为深受唐文化影响的吐谷浑人。此人身后有一棵大树,大树的右侧是一处汉式木构建筑,底部设有台基踏道,红色廊柱上有斗拱、梁架和出檐的庑殿顶,殿顶中央有一红色的宝珠,脊上两端有鸱吻,完全是汉式作风。将带有民族特色的帐篷和汉式殿堂同绘于一处相互并立,显示出唐朝汉文化和当地吐蕃、鲜卑、吐谷浑等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共生共存的场景,也是对死者身份和生活习俗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最好说明(图七)。
.jpg)
图七 泉沟一号墓后室西壁帐居图残存画面
由于乌兰泉沟一号墓没有文字资料出土,不能像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那样根据墓中出土的古藏文印章比定墓主的身份,但结合上述情况和墓中“暗格”出土的鎏金银质王冠,笔者倾向认为死者可能仍然是一位吐蕃统治之下的吐谷浑王公贵族,这顶具有浓厚中原文化色彩的“冕鎏型王冠”本身,也并非吐蕃系统的王冠式样。换言之,它并非吐蕃王朝所赐,而是死者生前遗物,在其死后作为死者最为珍贵的遗宝和另一件四曲鋬指金杯一同秘密地随葬于专门设计的墓葬“暗格”之中。其中深意令人玩味。
众所周知,青海本为吐谷浑人所建立的“河南国”故地,吐谷浑人自其立国之始,便和南朝萧梁、北魏、唐朝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受中原文化影响很大。吐谷浑王族及其统治者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在政治制度上也多模仿中原。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灭亡吐谷浑国,尽据青海之地,吐谷浑绝大部分为吐蕃所统治,时间长达170多年。此间一部分吐谷浑王族陆续归唐内附,如吐谷浑慕容诺曷钵部;另一部分仍然留居在青海故地的吐谷浑部族则成为吐蕃统治之下的小邦国,要定期向吐蕃纳贡,接受吐蕃的军事编制和劳役“大料集”,其上层王族也与吐蕃王室通婚,“结为甥舅之国”,如本文所述的2018血渭一号墓的墓主。乌兰泉沟一号墓墓主的情况很可能另有隐情,是否是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吐谷浑旧主,虽滞留在青海吐谷浑王国故地,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吐蕃文化(如在壁画中的人物都有“赭面”印记),而一方面却仍然坚守其衣冠旧制不改,即在保持其原有的鲜卑文化、吐谷浑传统的同时,又心慕唐朝,死后在墓中表现出大量中原唐代仪仗制度、冠冕制度等汉文化因素。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四、从墓葬随葬品看唐蕃文化交流与“高原丝绸之路”
虽然目前新出土的这批墓葬大多被盗,残存的随葬器物已经很少,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观察到若干青藏高原各族与中原唐朝的密切联系,以及通过以青藏高原为主线的“高原丝绸之路”与周边地区、国家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实物史料。鉴于上述墓葬正式的考古报告尚未出版,笔者只能就其目前已披露的信息择要略加评述。
墓中出土的各类器物,从其性质上可以粗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死者生前曾使用过的“生器”,另一类则是专门为死者下葬入圹制作的“明器”(也作“冥器”)。即使遭到严重的盗窃,残余下来的随葬器物中也有不少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据报道,拉萨当雄吐蕃墓地中的大型墓出土有金银器、狗头金、青金石、玛瑙、珊瑚、绿松石、玉石、珍珠等饰件,以及陶器、铜器、铁器残件,漆器残片,贝类制品,擦擦,织物,以及石质黑白围棋子等。这当中黑白两色的围棋子的发现,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认为其与唐代中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之时,便将中原的琴棋书画、佛道占卜、农工百艺输入到了吐蕃,作为中原文人雅士文化身份象征的围棋在吐蕃高等级墓葬中的出土,无疑是唐蕃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吐蕃王朝文化中具有中原文化“底色”的实物证据之一(图八)。
.jpg)
图八 当雄吐蕃墓出土围棋子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被盗严重,除在“暗格”内出土了鎏金银质王冠和金质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杯这两件堪称国宝级的“重器”之外,也出土有多件鎏金银带饰、丝绸残块、珠饰等遗物。其中最能体现中原文化色彩的器物是一顶王冠。王冠前檐缀饰有珍珠冕旒,4个冠面上的纹饰图案正面与背面相同,为双龙吐水,龙体肩生双翼,双龙足踩莲花;王冠的两个侧面各饰有一立凤站于莲花座上,龙凤图案的周围环绕以联珠纹团花、蔓草、忍冬纹等北朝至唐代流行的装饰性纹样图案。仝涛先生认为:“该王冠与唐朝皇帝的礼冠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尤其是冠前檐所缀珍珠冕旒,乃是中原王朝统治者所戴冕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其说可从。在既往发现的吐蕃金银器当中,曾经发现过可能与吐蕃高级别王公贵族所戴王冠相似的遗物,但从总体风格上看不是这种“冕旒型王冠”,而与蒙古高原和欧亚草原发现的匈奴、突厥式王冠样式近似。因此,将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的王冠归入中原王朝冠服制度来考虑,大方向是正确的。
青海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即便是在被盗严重的情况下,出土器物仍然是近年来青藏高原发掘的吐蕃时期墓葬中最为丰富的。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大量制作精美的金银器、丝绸、各类宝石镶嵌的首饰等高级奢侈品。金银器当中的金鋬指杯、胡瓶,都是这个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典型器物,往往作为赏赐、交换和贸易的“国之重器”,在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中均不罕见。尤其是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镶绿松石金凤钗、镶绿松石金链、镶红蓝宝石双狮日月金首饰等饰件,工艺水平极高,制作极其精美,堪称吐蕃系统金银器当中的极品。鎏金银饰片中塑造的动物形象多具有欧亚草原文化的风格,如镂空方形大角鹿、装饰在鎏金马鞍前后桥上的狮子、奔鹿、翼马等,与过去被盗掘出土的同类器物可以参互比较,让人们从不同的层面观察到吐蕃金银器与中亚波斯萨珊、粟特和东方唐代金银造型艺术之间的彼此交流借鉴,也更令人信服地展示出吐蕃艺术家们基于本土文化的独特创造。
墓中出土的纺织品残片据统计共有836片,种类包括纱、绮、绫、绢、织锦等,图案纹饰多为唐代流行的团窠状,纹样可见植物、动物、几何形装饰纹样等类别。结合以往都兰热水墓地出土织物的情况综合分析,这些丝绸织物上的狮子、对鸟、葡萄等纹样均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流行和喜爱的纹饰,当中既有唐朝内地织造之物,也有直接来自中亚波斯、粟特等地的织锦,由于吐蕃本土不具备生产丝绸的自然和工艺条件,这些织物往往通过唐代中央王朝的赏赐、丝绸之路上的交换、商贸,或者通过战争、掠夺等不同的方式传入青藏高原,成为高原各族倾慕中原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是“高原丝绸之路”最为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五、结语
考古学是历史的另样书写方式。它通过发掘出土的实物史料(包括遗迹和遗物),如同社会历史的一个个“切片”,提供给我们观察已经消逝的历史时空的若干实物标本和“横截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成果为更好地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青藏高原考古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展阶段,就是吐蕃王朝时期考古(或可简称为“吐蕃考古”)的不断发展并获得新的成果。这个时期西藏高原各部族逐渐形成统一的吐蕃王朝,并创立了文字、城堡、陵墓,形成地方性政权,借鉴中原和周边民族的文明成就形成各种制度文化,进入有史可载的西藏历史时期,揭开了西藏文明史的新篇章。而其中最能体现吐蕃王朝最高统治者意志、最具地方性政权政治意义的考古遗存,莫过于都邑、城堡、宗教或纪念性建筑、陵墓等王权和社会等级的象征物。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考古学正在用实物史料不断书写西藏古代史的新篇章,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通过本文所论近年来吐蕃墓葬考古的新发现,可以从中窥见青藏高原本土文化因素和来自中原、河西地区的文化因素相互交织相融,重现7—9世纪生活在青藏高原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若干历史场景中的片断,同时也为进一步认识吐蕃时代的墓葬制度与丧葬习俗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吐蕃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纺织品等高级奢侈品,也从丰富的物质层面讲述了高原各族人民以宽阔的胸怀、开放的心态融入以东方唐王朝为中心的欧亚文明体系,开创和建设“高原丝绸之路”,从而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密切交流的一个个“中国故事”,必将传之久远。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4期
为便于微信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