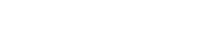作者简介:
张长虹,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藏昌都和青海玉树地区都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佛教石刻,既有造像又有刻经。文章梳理出其主要刻经内容有:《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无量寿宗要经》《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通过对汉、藏文大藏经和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同名佛经的整理分析,发现这些佛经均有藏、汉译本,不仅保存在汉、藏文大藏经中,在敦煌文献中也均有发现,是在吐蕃时期就已经译出并且非常流行的经典。根据同出的古藏文纪年题记信息,西藏昌都察雅仁达和青海玉树贝沟石刻佛经的年代为公元9世纪初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这些佛教石刻的出现应是吐蕃王室推行佛教政治的产物,反映了吐蕃时期汉藏佛教间的密切互动与深度交融。
关键词:青藏高原东部;古藏文刻经;吐蕃时期;汉藏佛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西藏昌都、青海玉树等地,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这些摩崖造像同时共存的还有古藏文题记,既包含有重要的历史信息,也有佛教刻经,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这些题记进行收录研究,但对于其中的佛经部分不但有遗漏,并且研究不够充分。基于此,本文对这些古藏文佛教刻经进行专门整理,并探讨其所反映的吐蕃时期的佛教面貌。
一、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古藏文刻经
(一)西藏昌都察雅仁达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在西藏昌都市察雅县香堆镇仁加村仁达崖壁,发现了高浮雕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造像,造像的下方和右侧共刻有3组古藏文题记,第一组位于造像下方,4行,是讲修习正法之功德;第二组位于第一组下方,10行;第三组位于造像右侧上方,18行。其中第一组和第三组与《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有关,第二组则言明了造像时间、缘由、工匠、目的等,系雕刻于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的猴年,即804年。早在1988年,恰白·次旦平措就用藏文发表了第一组和第二组的题记录文,郑堆、丹增把这篇论文又译成汉文发表。同年对这一录文进行公布、翻译的还有马林,此后不断有学者对这两组题记进行收录和研究。但是关于第三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古藏文题记则未见有人抄录、公布和翻译,仅在《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一书有一张黑白照片公布。第三组的18行古藏文题记为简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约有48句,若按每颂4句,则计12颂,每句7字。目前没有找到与之相同或相似的版本。但其中的句子可以在全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中找到意义接近的句子,如其中的“ལུས་ངག་ཡྀད་ཀྱིས་ཕྱག་འཚལ་ལོ”对应于“ལུས་དང་ངག་ཡིད་དང་བས་ཕྱག་བགྱྀའོ”,“ དམ་ཆོས་འཁོར་ལོ་བསྐོར་བར་བསྐུལ”对应于“འཁོར་ལོ་བླ་ན་མེད་པ་བསྐོར་བར་བསྐུལ”,等等。可以看出,尽管内容简短,但均在全本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句子,因此推测该石刻本是为了适应崖面有限的空间而精心选取的一个本子,其母本应源自吐蕃时期流行的藏文译本全本,但十分精简,堪称是《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精简石刻本。
(二)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在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约130米处的一块崖壁上,阴线刻有36行古藏文题记,内容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其中第1—8行为普贤行愿陀罗尼,第9—36行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多位学者都对这一处题记进行过收录,最新的整理校勘是四川大学考古队的现场识读、抄录和翻译。这部石刻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是一部完整的版本,共有60颂,每句9字,有对应的汉、藏译本存在。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亦译为《普贤菩萨行愿赞》,在吐蕃时期的译经目录《丹噶目录》(No.470)和《旁塘目录》(No.442)中均有收录,均记作97颂,表明该经在吐蕃时期已经译出。该经还见于《大方广佛华严经》最后一品,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华严部,末尾注明由印度堪布Jinamitra、Surendrabodhi和益西德翻译。这几位都是吐蕃时期有名的译师,益西德据称是吐蕃时期翻译佛经最多的人。此外,在《甘珠尔》陀罗尼集中收录有单篇的偈颂经文。在《丹珠尔》杂部最后汇集的祈愿、吉祥类中也有收集。《甘珠尔》和《丹珠尔》所收的3个版本内容几乎完全相同,都为62颂,每句9字。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也发现不少《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及注疏写本,有学者统计共52件。敦煌藏文写本一般为60颂,每句9字,如法藏敦煌写本P.T.45、P.T.116和英藏敦煌写本ITJ 25,均为完整的藏文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均为60颂,每颂4句,每句9字。藏文大藏经所收与敦煌写本中的内容十分接近,只有个别用字不同或语句顺序不一致,且最后多出2颂。有学者认为初译本只有60颂,多出的偈颂是印度论师和吐蕃译师添加的。《丹噶目录》和《旁塘目录》记作97颂,似是将后缀的其他经文也算入了其中。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汉译本也有多种,收录于《大正藏》中,也见于敦煌汉文文献。《大正藏》所收的汉译本有唐代不空译《普贤菩萨行愿赞》,计有62颂,每颂4句,每句7字,偈颂后面还有八大菩萨赞和普贤行愿陀罗尼。62颂的《普贤菩萨行愿赞》也见于唐代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卷之《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大正藏》还收录有两部敦煌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No.2907和No.2908,为英藏敦煌本S.2361和S.2384,均为60颂,每颂4句,每句7字。敦煌文献中的汉文《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目前据统计有28件,其中不乏保存完整者,如国家图书馆藏BD3355(2)、BD6056(1)、BD7347和英藏S.275等,一般为60颂,每句7字。其中P.3568卷首题“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奉诏译”,表明该汉译本是吐蕃高僧无分别所译。
玉树贝沟的石刻古藏文《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共60颂,每颂4句,每句9字,其内容与敦煌写本几乎完全一致,仅有个别用字、用词不同,一句中字词顺序不同和个别语句顺序不同。如与ITJ 25相比较,第5偈第一句,贝沟石刻本为“མེ་ཏོག་དམ་པ་ཕྲེང་བ་མཆོག་རྣཾས་དང་།”,ITJ 25为“མེ་ཏོག་དམ་པའ་ཕྲེང་བ་དམ་པ་དང་།”,两句分别用了不同的词:མཆོག་རྣཾས和དམ་པ,但两者意思相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第25偈第2句,贝沟石刻本为“བདག་གྀས་རྟག་ཏུ་རྒྱལ་བ་མངོན་སུཾ་བལྟ།”,ITJ 25为“མངོན་སུམ་རྟག་ཏུ་བདག་གྀས་རྒྱལ་བར་བལྟ།”,这两句仅是词的顺序不同。再如第58、59偈,这两偈的8句,按ITJ 25中第1—8句的顺序,在贝沟石刻本中的顺序则为5、6、1、2、3、4、7、8,也就是说第59偈的前两句被前置到了第58偈的前两句。这些细微的差异不影响贝沟石刻本的完整性以及其与敦煌藏文写本的一致性。藏文大藏经中所收的版本与敦煌写本几乎一致,只是多出了两偈,其内容与汉译本也可以大致对应。汉译本尽管存在多个不同的译本,但可以看出各译本之间明显的相似性。如《大正藏》No.2907所收敦煌本S.2361开头第一偈为“尽诸十方世界尊,善游三世人师子;我身口意具清净,是故今当遍稽首”。大多数敦煌写本与此译本相同。《大正藏》No.2908所收敦煌本S.2384则为“应在十方刹土中,游于三世人师子;彼等诸佛我无遗,以净身口意稽首”。不空译本为“所有十方世界中,一切三世人师子;我今礼彼尽无余,皆以清净身口意”。般若译本为“所有十方世界中,一切三世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尽无余”。这4句在藏文译本则比较一致地呈现为“ཅྀ་སྙེད་སུ་དག་ཕྱོགས་བཅུའྀ་འཇྀག་རྟེན་ན། ། དུས་གསུམ་གཤེགས་པ་མྱྀའི་སེང་གེ་ཀུན། ། བདག་གྱྀས་མ་ལུས་དེ་དག་ཐམས་ཆད་ལ། ། ལུས་དང་ངག་ཡིད་དང་བས་ཕྱག་བགྱྀའོ། །”。因此可以推断,贝沟石刻本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已经流行,目前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写本中能够找到多件与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者,并且当时有多种对应的汉译本流行。
(三)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石刻《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
距上述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约百米距离处,为贝沟大日如来佛堂,高浮雕有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造像,其旁边的崖壁上,阴线刻有两段、23行古藏文题记,第一段计有18行,第二段有5行。其中第二段的题记被复制再刻于一块石板上,嵌于佛殿内的一面墙壁上,即有名的“狗年题记”(806年),学界早有公布,多有研究。第一段题记的内容是对大日如来及众眷属的赞颂,近年的考古调查简报已有公布。这是一部石刻的经文《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与紧邻的9尊浮雕造像是一体的,可以说是该处造像的文本依据。在这部石刻本的《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中,第一部分是对大日如来及其所居佛刹和莲花、狮子、菩提树的赞颂;第二部分是对八大菩萨的赞颂,八大菩萨的出场顺序依次为:观音菩萨、弥勒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文殊菩萨、除盖障菩萨、地藏菩萨。各偈颂长短不一,最长的是对大日如来的赞颂,多达19句,最短的是对狮子的赞颂,仅有3句;对各菩萨的赞颂也是4—9句不等,其中对普贤菩萨的赞颂最长,达9句。各偈颂每句均为9字。
在吐蕃时期的译经目录《旁塘目录》(No.420)和《丹噶目录》(No.437)中均收录有一部《圣薄伽梵大日如来及眷属八菩萨赞及明咒二卷》,这部经布顿大师亦有收录,并注明译者为却季协饶(法智)。《旁塘目录》(No.674)中在赤松德赞所撰目录下面还有一部《圣大日如来、释迦牟尼及八菩萨赞》,但在《丹噶目录》中未见收录,布顿大师有收录。说明该经也在吐蕃时期已经译出。在敦煌古藏文写本中,也发现有《毗如遮那及眷属赞》,如法藏P.T.7AV、P.T.108,英藏ITJ 67,这3个版中P.T.108首全尾残,P.T.7AV首残尾全,ITJ 67仅有1叶,但从其内容看,三者出自同一译本,内容相同,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赞颂长短一致,每颂均为8句,每句7字。该赞颂的内容和长短同贝沟石刻本不一样,但八位菩萨的出场顺序是一致的。
与贝沟石刻古藏文《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完全一致的汉译本目前还没有见到,但《大正藏》中收录有一部唐代不空译的《八大菩萨曼荼罗经》,是八大菩萨曼荼罗的供养观行法,给出了八大菩萨的名号、座次和身色、印契、执物、坐姿等图像学特征,其中八位菩萨的名号和出场顺序与贝沟石刻本一致,以往学者们在研究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的图像组合时常常引用此经。该经后半部分为“八大菩萨赞”,与不空译本《普贤菩萨行愿赞》后面所附的“八大菩萨赞”完全一致。
(四)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无量寿宗要经》
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石刻是一处大型的集阴线刻佛传故事、古藏文题记为一体的佛教考古遗存,在各组石刻场景的中央位置,阴线刻有《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无量寿宗要经》,分别编号C组和B组题记。以往学者对这两部经也有收录,最早最完整的是高瑞(གཉའ་གོང་དཀོན་མཆོག་ཚེ་བརྟན)在《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年第4期公布的青海玉树贝纳沟、勒巴沟发现的佛教摩崖石刻,其中就包括这两处佛经石刻题记,后来又收入其著作《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中。此后巴桑旺堆、恰嘎·旦正等先生也均有收录。不过迄今录文公布最完整并提供了可靠汉译文的是青海、四川联合考古队于2017年发表的调查简报。
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无量寿宗要经》刻于B组佛诞图的右侧下方,共15行。第1—2行为题名;第3—8行为经咒,共16句;第9—15行为持诵该经咒的功德。《无量寿宗要经》是吐蕃时期最为通行的一部经,在敦煌藏文写卷中,该经数量最多。据最新统计,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数量为2281件,并且该经是由王室赞助,抄写于9世纪20—40年代。在敦煌汉文写卷中,该经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是隋唐时期流传最广的六部经卷之一,总计有977卷。这部经因为数量多、文本全、分布分散,吸引了全世界的学者对之进行研究,青海民族大学桑吉东知对此有很好的研究综述,兹不赘述。
《丹噶目录》和《旁塘目录》中均未发现该经,但《大正藏》目录No.936《大乘无量寿经》处注明“唐法成译”。王尧先生也提出“《大正藏》936号,法成根据藏文译成汉文本。原为敦煌写本”。法成在沙州的活动年代约为833—859年。藏文大藏经中收录有两部完整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题名为“འཕགས་པ་ཚེ་དང་ཡེ་ཤེས་དཔག་ཏུ་མེད་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原德格版编号No.674、675),不同于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本的题名“ཚེ་དཔག་ཏུ་མྱེད་པའྀ་མདོ་སྡེ། ”,但其内容同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写本类同。目前学界将敦煌文献中的藏文写本《无量寿宗要经》分为甲本和乙本,如《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24、125、126册中收录的藏文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每一部均标注了甲本或乙本,咒文较长的为甲本,短的则为乙本;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有些也标注了甲本或乙本。黄明信统计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收227个藏文写卷中,甲本145卷,乙本82卷。近年,夏吾措和桑吉东知在研究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时,按照经文的差异和咒语长短,将之分为甲乙丙丁4种。敦煌发现的大量汉文写本《无量寿宗要经》也被分为甲本和乙本,左丽萍统计出汉文敦煌写本《无量寿宗要经》甲本1200件,乙本6件,绝大多数为甲本。《大正藏》所收No.936《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即为敦煌本甲本。日本学者上山大峻曾经将不同的汉藏写本进行了简单比较。笔者也撰文对汉、藏大藏经版本,敦煌写本和本文讨论的石刻本《无量寿宗要经》进行了对勘。
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本《无量寿宗要经》同西藏昌都察雅仁达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一样,也因崖面空间所限,刊刻内容十分精简。《无量寿宗要经》全本的内容可分为5部分:一、缘起;二、若干千万佛一时同声说此经(汉藏文各本中具体数目有所不同);三、咒语(每当说完该经的一种功德,即出现一段同样的咒语,反复出现多次,各本出现的次数不完全相同,有24次、30次等,各本中咒文的长短也有所不同);四、分说书写持诵、布施供养此经的功德(功德一般有18种或16种,各本亦有不同);五、偈语(共6段,各本中也是长短不一)。该石刻本仅保留了经文的核心部分,即第三、四部分,略去了第一、二、五部分。其中功德部分也是大大缩略,只有简短一句,也没达到16种。咒语部分相对较为完整,因为该咒语本不算长,最长的版本为18句,最短的有13句,此处为16句。介于两者之间。吾娜桑嘎石刻本尽管是精简本,但其咒语和功德大部分可以在各种完整的藏、汉译本的《无量寿宗要经》中找到,其母本应是源自某个《无量寿宗要经》藏文译本的全本。
(五)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该经刻于前述《无量寿宗要经》的旁边,位于整个石刻点的正中央位置,分布在一块高大平整的崖面上,共有28行,最下方还有一句六字真言,是一部完整的石刻本《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下文简称《般若心经》)。
《丹噶目录》(No.14)和《旁塘目录》(No.15)中均收录有该经,均记作28颂。表明该经在吐蕃时期已经译出,现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的般若部(No.21)和十万怛特罗部(No.531)。根据该经译跋,译者为印度堪布离垢友(བི་མ་ལ་མི་ཏྲ། Vimalamitra)和译师比丘仁钦德(རིན་ཆེན་སྡེ),由主校译师格洛(དགེ་བློ)和南喀(ནམ་མཁའ)等校订。在敦煌藏文文献中,《般若心经》写本的数量也不少,仅《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就收录有70多件。《般若心经》根据内容可分为大本和小本,也称为广本和略本,大本具足序分、流通分和正宗分,小本只有正宗分。其中藏文大藏经的版本和法藏P.T.449、451、457、494、495等为大本,其他法藏敦煌藏文写本则为小本,小本的数量远远多于大本。
《般若心经》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乘般若类佛教经典,在中国非常流行,先后被译成汉文达21次之多。玄奘的260字《般若心经》更是家喻户晓。各种汉译本中,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本为小本;此后法月、般若共利言、法成、智慧轮的译本均三分具足,称作大本。如法藏P.4882《般若心经》,卷首题名“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般若心经》由于流行程度广、各语种文本丰富,研究比较充分。荷兰莱顿大学斯尔克曾对14种不同版本或抄本的藏文《般若心经》进行了仔细的对勘研究;沈卫荣曾将藏文大藏经收录的两种藏译本与法成和施护的汉译本进行对勘;才让对《般若心经》的藏译本进行梳理,将大本又分为大本甲类和大本乙类,并对P.T.449进行了专门研究。禇俊杰在王尧对勘藏、汉《般若心经》的基础上,又对藏文大藏经本和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中的语词进行了研究。笔者在考古调查简报中也对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的石刻本与几种汉藏译本进行了简要对勘,认为其与法藏P.T.494较为接近,译成汉文后,与法成译本比较接近,是一部藏译本大本。
二、几点观察
通过对上面在西藏昌都、青海玉树等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石刻古藏文佛经的整理,我们发现它们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这批刻经均反映了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的密切互动与深度交融
目前发现的这几部刻经均既有藏译本,也有汉译本,并且《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全本、《无量寿宗要经》全本和《般若心经》大本均有内容相同的藏、汉译本可相互参照,存在藏汉互译的情况。法藏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根据卷首题名是由吐蕃沙门无分别奉诏译,无分别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42—约800)时期的一名高僧,《布顿佛教史》中收录有多部他从梵文、汉文译成藏文的经典,如《佛说回向轮经》就是由汉文译出,这些表明他兼通藏、汉、梵等多种语言文字,不仅将汉文的经典译成藏文,也将藏文的经典译成汉文。法藏P.4882《般若心经》根据卷首题名是由吐蕃高僧法成译成汉文,《大正藏》目录No.936号《无量寿宗要经》也注明“唐法成译”。法成也是吐蕃时期的著名高僧,活跃于9世纪上半叶,在河西地区长期从事佛教活动,吐蕃经卷里前后出现他的署名约20处。王尧先生对法成从藏文译成汉文、从汉文译成藏文的经目进行了梳理。吐蕃时期活跃着一批像无分别、法成这样的高僧,精通多种语言,将梵文、汉文、于阗文等不同文字的佛经翻译成藏文,同时也将藏文佛经译成汉文,推动了汉藏佛教的深度交流与融合。除了这些文化精英,当时还有非常多的地位低下的写经生,兼通汉藏双语,不仅有汉族,还有藏族和其他民族。如法藏P.T.470—477《般若心经》藏文写卷绝大部分是一个叫(张)进达(译音)的汉人书写的。抄写了数十卷《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生名录中,张略没藏是一个少数民族。敦煌吐蕃经卷显然是多民族协作的产物。西藏昌都察雅仁达石刻除藏文题记外,还有一组汉文题记,表明汉族工匠也参与了佛经和造像的刻造。
(二)这几处刻经是吐蕃王室践行佛教政治的产物
在西藏昌都察雅仁达和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的刻经处同时刻有纪年题记,记载了刻经造像的时间、目的和功能。两处石刻的年代均为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前者为804年,后者为806年,年代接近;造像题材相同,均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刻经内容也相似,分别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全本和精简本。仁达石刻第二组题记提到“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封授比丘为佛法和议政大臣之衔,赐金子以下告身。王妃钦氏列莫赞等众多王室成员和臣民入解脱之道,命宰相比丘……以及内臣论韦·赤松热朵赞等开始着手与唐议和之事。故,堪布巴廓·益西央、比丘……为赞普之功德,众生之福泽,雕刻佛像与经文……”。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石刻题记记载“狗年,浮雕众佛像及缮写如上所有经文之祝愿等,为今上赞普赤德松赞之世君臣、施主及一切众生之故也。此乃比丘大译师益西央主持……众生之任何人或目睹、或触摸、或礼敬、或听闻、或忆念,其福德及智慧之力,均回向赞普父子及一切众生,登于无上菩提也。此愿!”从题记可知,这两处造像和刻经均由比丘大译师巴廓·益西央主持,是为了赞普之功德,众生之福泽;其建造背景是为了“开始着手与唐议和”。关于这一点,多名学者已经有了精彩论述,不再赘述。两处题记中多次提到“封授比丘为佛法和议政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大译师益西央”等,可知此时僧人在吐蕃地方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力,青藏高原东部这批在益西央主持下雕刻的佛经和佛像很可能就是得到了吐蕃王室甚至是赞普本人的授意与大力支持。吐蕃自赞普赤松德赞时起尊崇佛教,以桑耶寺为倡佛根据地,在吐蕃各地广建塔寺、制作佛像、供养僧人、资助翻译和抄经,以佛僧为宰相,兴佛证盟、建立僧官体制等,符合“佛教政治”九大特色中的大部分。其子赤德松赞在他的基础上将佛教政治更推进一步,继续崇佛抑苯,以僧人为相,以佛法理政,在青藏高原东部刻经造像,玉树贝沟等地大日如来穿上吐蕃赞普的服装,将佛与赞普等同,等等。这些都是践行佛教政治的产物,从中也可看出唐朝对其的影响。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汉藏佛教传统中都是一部与王室信仰密切有关的经典。法藏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是无分别奉赞普之命译出的。不空和般若的汉译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是奉皇帝之命翻译,不空本人也在唐代受到皇室重用。《无量寿宗要经》同样与王室和赞普有着密切关系,是为赞普积福而写。法藏P.T.999记载:“作为天子赤祖德赞之功德,在沙州写造了汉、藏文的经典《无量寿经》,作为对臣民的广泛的教法大布施……作为王后赞蒙彭母子之光护(微松)宫殿之功德……依据宫廷的指令及信函……作为教法大布施的资具,从龙兴寺的经籍仓库中,取出汉文《无量寿经》135卷,藏文480卷,总计615卷,散发给众人……”这里的《无量寿经》即指《无量寿宗要经》。从这份文书可以看出,《无量寿宗要经》因为是为赞普积福,因此抄经所需费用可能都由王室资助,管理上也更为严格,抄经质量也胜于其他经文。青藏高原东部出现的这几部刻经都与王室、赞普有关,应该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是与吐蕃以佛教理政,王室和赞普亲自介入抄经、刻经、造像等活动密切相关的。
(三)青藏高原东部的刻经内容和造像题材反映了与河西地区相似的佛教实践
昌都察雅仁达石刻和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石刻,不仅刻经内容相似,均有《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并且造像题材也一模一样,均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玉树贝沟还有刻经《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为造像的文本依据。这些刻经和造像的出现表明《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与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是常被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佛教实践。这在敦煌古藏文写本中也可找到佐证,如法藏P.T.7A是多种经组合在一起的一个文本,显然是用于佛教的修习和实践,其中就有这两部经。
由不空于756—774年之间译出的《普贤菩萨行愿赞》,在普贤菩萨行愿赞的后面就是八大菩萨赞,然后又是普贤行愿陀罗尼,并且八大菩萨的名号和出场顺序与藏东刻经和造像中的一致。《普贤菩萨行愿赞》中的八大菩萨赞与不空翻译的《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内容是一样的。在敦煌石窟壁画和绘画中,也发现不少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题材,最有名的为榆林窟25窟,此外还有莫高窟第14窟、榆林窟20窟等,很可能是受到了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的影响。相似经典的出现、相同题材的图像出现,反映了两地之间相似的佛教实践。
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这批古藏文刻经均雕刻于9世纪初的吐蕃时期后期,为我们提供了除大藏经版本和敦煌写本之外另一种比较可靠的版本,他们同造像一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不应被忽视。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4期
为便于微信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